记忆似海,只有不停地洄漩和逐流,才有其生命的价值,那些从浪尖上逃逸的结果,或就是遗忘,一切都在时间的属性中,随着圈圈指针被永久奠定或分崩离析。 遗忘是可耻的,小小年纪应努力去开拓更广阔的记忆空间,无论是被赞美还是批评,都容易让人从晕乎乎的课堂上打起精神,男孩子忙于复杂的计算题,女孩子更爱通篇大背诵。 “一定要走到那棵小树跟前再休息!”指导员王吉文望着前面四五百米处一棵小树,又暗暗地下了一次决心......” 那一次,班长一肩乌黑的长发,声情并茂,流利的画面一帧帧扑来。 “在那白云下面,一长串大雁正排成‘人’字形的队伍,轻轻地向南飞去。它们靠得那么紧,排得那么整齐。” 短暂的沉默之后,全班一片哗哗击掌,而这些个掌声,相形于我那结结巴巴、断断续续的表现力来说,就像冷冷地拍打在脸上,令人找不到可钻的地缝。 我应是朝她上看下看左看右看了去,想要搜遍这份魔力的来源,也亟待着需要一份美好的想像,来平衡自己,不知不觉,便油然而生了一个“假如记忆力可以移植”的命题,这种阿Q精神,恍忽了我整堂课程,以及由此开拔的流年。 时光苍狗,世事变迁,如果说生活是由酸甜苦辣组成的,倒不如说只是一场分色的记忆,每当感叹时,我仍然会以这样的假想来托底,来平仄相兑。假如记忆力可以移植,移出的必然是我的阴霾和不爽,移入的必然是阳光和欢情。或者类同于还原出一个真正的张东引,少年老成,天赋异禀。
鉴于对约翰纳什的喜欢,需要移入一个真实的查尔斯,与之同行同梦,添加更多的委婉和交流,向艾丽西亚致敬,悉数每一个体贴的细节,传递出豁达的美丽心灵。 至于喜欢我的人,就比如花范月,可以从一个名字开始,植入好奇,抱以欣慰,做好清空一段街区的准备,等待更多的形容填充空白,或许把酒问月、对月当歌的一天不会遥远。如此,我一样有说:“请让我,也喜欢上你。”并期待你一低头的娇羞,瞬间带给我理想中的车水马龙。
假如记忆力可以移植,或用于自我疗伤,或用于良好的祝愿,再怎么移植,都希望能抱有一种真诚的向往,不装不作,直面人生。
| 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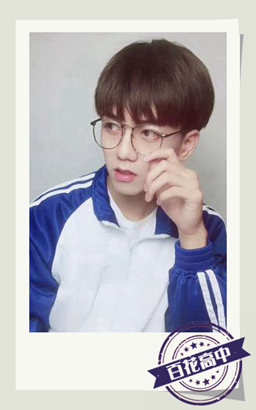

![]() 苏公网安备32030302308112号 )
苏公网安备32030302308112号 )